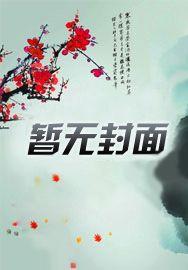我看书斋>觉醒系统:四合院里享受生活 > 第200章 聋老太太下线(第2页)
第200章 聋老太太下线(第2页)
但更多的人,是对陈小满投去感激和敬佩的目光。
他了大财,却没忘了老邻居,关键时刻真肯出力,办事还如此周到,给足了易中海和傻柱面子,也全了全院人的体面。
聋老太太的灵堂很快搭了起来,老人的遗像摆放在正中,面容慈祥。
傻柱披麻戴孝,以孝子的身份跪在灵前答礼,易中海则以主事人的身份忙前忙后。
陈小满提供的丰厚物资和支持,让这场原本可能因经济原因而略显简陋的丧事,办得庄重、体面、哀荣备至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陈小满站在忙碌的人群中,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
他的“享受生活”,在此刻有了更深层的含义,那是一种基于强大能力和经济基础之上,对传统人情世故的深刻理解和尊重,是一种“达则兼济”的格局与担当。
他用自己的方式,风风光光地送走了这位见证了整个四合院变迁的老人,也赢得了老街坊们自内心的尊重。
天色灰蒙蒙的,透着寒意。南锣鼓巷号院内外,早已聚集了不少人。
街坊邻居们大多都来了,臂缠黑纱,神色肃穆。
陈小满安排的黑色灵车静静地停在胡同口,庄重而气派,引得不少路过的人驻足观望,低声议论着这是哪位大人物的排场。
院里,简单的告别仪式正在进行。
聋老太太的棺木是上好的楠木,厚重润泽,这是陈小满连夜让人送来的。
棺木前摆放着供品和老太太的遗像,照片上的老人笑容慈祥,仿佛仍在看着这个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大院。
易中海作为主事人,强忍悲痛,简单讲述了老太太的生平,无非是些“一辈子不容易”、“与人为善”、“是咱们院里的老寿星”等朴素的话,却引得不少老街坊再次落泪。
傻柱披麻戴孝,作为实际的养老送终人,跪在灵前,哭得不能自已,几次都要旁人搀扶。
这个平日里咋咋呼呼的厨子,此刻将所有的悲痛和不舍都宣泄了出来。
陈小满和安雨琪站在人群前列,穿着深色的衣服,神情庄重。
陈爸陈妈、陈小雪、陈小雨两家也都在。
陈小满没有过多言语,但他的存在本身,就是一种无声的支持和力量的象征。
仪式结束,起灵的时候到了。
八个壮实的杠夫上前,稳稳地抬起棺木。
“老太太,起驾喽——”一位年长的执事人拖着长音喊了一句。
顿时,哭声大作。
傻柱被人搀扶着,捧着遗像,走在最前面。
易中海夫妇紧随其后,老泪纵横。
然后是陈小满、安雨琪等晚辈,再后面是全院的老少邻居们。
送葬的队伍缓缓地走出号院,走过南锣鼓巷。
许多相邻胡同的老街坊听到动静,也自地站在门口,默默行注目礼,送这位有名的老寿星最后一程。
这场面,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胡同里,已算得上相当隆重和体面。
陈小满安排的几辆小轿车跟在队伍后面,负责接送年纪大的和身体不便的邻居去殡仪馆。
贾家人也都在队伍里。
贾张氏看着这排场,看着那气派的灵车和跟着的轿车,再看看走在最前面、被众人簇拥着的陈小满,嘴唇动了动,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酸话咽了回去。
在这种场合,即便是她,也知道有些话绝不能出口。
但她心里那点不平衡,却又加深了一层:凭什么好事都让他陈家占了?
连办个丧事都能显出他的能耐?
秦淮茹搀着婆婆,低着头,不知在想什么。
贾梗和贾槐花则更多的是茫然和一种参与重大事件的拘谨。
到了殡仪馆,一切流程都已由陈小满的人提前打点好,井井有条,避免了所有的忙乱和尴尬。
易中海和傻柱只需要按照指引完成仪式即可。